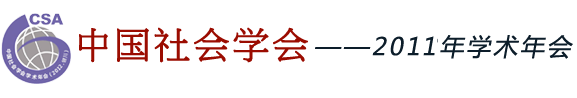经中国社会学会批准,2011年中国社会学年会设立“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社会政策研究”分论坛。本论坛由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室共同主办。论坛主持人谢建社教授,会务组先后收到论文近60篇,经过专家评审通过49篇。本论坛于2011年7月22-25日在江西滨江宾馆召开,与会代表踊跃发言,阐述了许多学术观点。
与会学者就创新农民工管理与服务模式、农民工管理纳入社会管理体系、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政策、农民工政治参与、农民工职业培训、农民工社会网络建构、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积极回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新诉求,从制度与政策层面帮助其解决“融城难”问题,是地方政府和社会面临的新挑战,也是学者研究面临的新任务。广州大学谢建社教授、赖建锋研究生、万春灵研究生等以广东近期发生的两起外来人与本地人的冲突事件为例,阐述创新流动人口社会管理服务的广州模式,第一,“一盘棋”模式。“一盘棋”管理模式。流动人口管理由过去的“编外管理”、“补缺管理”、“出租屋管理”、“监控管理”到“接纳管理”、“融合管理”再到“管理服务并重并举”。第二,“契约化”模式。“契约化”模式,即以“出租房屋契约化”管理作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的模式,通过服务型政府的引导,以居住地为管理抓手,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核心纽带作用。第三,“大统筹”模式。该模式以资源整合为手段,以社会化管理为途径,实现了由以社会控制为主的治安管理模式向城市统筹规划、综合服务管理模式的转变,体现统筹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思路,强化流动人口管理的服务职能。第四,“积分制”模式。流动人口所属城市按照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以积分排名的方式为外来流动人员安排一定数量的入户指标,入户的流动人员子女可入读公办学校就读,这标志着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流动人口管理创新一大进步。河南省社科院李怀玉副研究员基于对河南省5个地市的实地调研资料分析,认为农民工的社会管理工作没有跟上时代需要,农民工城市社会管理体制严重滞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陈天仁教授通过对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街道辖区内331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对上海城市社会管理与服务提出了很好和对策。因此,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高社区服务和管理水平是政策制定的基础。
农民工真正的融入城市生活,确保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艰巨任务。而融合性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融合的重要载体,是特定时期和背景下的一种新的组织形态。中共余姚市委党校陆银辉讲师通过对宁波市的余姚新老居民和谐联谊会的考察,探讨融合性组织在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融合中的作用。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失衡是事实上阻碍劳动力跨越城乡流动的重要原因,它的不对称性主要体现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和就业信息等方面上。既然公共产品不对称是劳动力城乡统筹的最大障碍,那么就应考虑移除—公共产品均等化即为相应的思路。广东嘉应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孙博副教授认为,欲把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动纳入统筹范围之内,亟须抓紧的一项工作就是农民工会的建设。“直选工会+项目工会”的模式较为适合农民工随机灵活的打工特点,且可以兼容非农流动劳动力。期望的劳动力流动应该是计划配置、市场配置与自动配置在更高层面的合理结合与配合。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新研究员等认为,除了用工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因素外,技能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障碍,技能培训在其中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迫切需要各级政府部门作出必要的制度安排。因此,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是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周晓津助理研究员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前后的福利变化进行经济学分析,从劳动力生命周期的角度给出了中国农民工市民化最低成本的一般化理论模型,并以广州为例给出一种简化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一般化理论模型还可用于外来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析。利用DEA(数据包络分析)对自1978至2007这30年间的中国整体失业率进行估计,尝试从模型化的角度对中国的整体失业率进行描述和估计。
伴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产生与壮大,我国农民工政策从1984年中央文件首次规定农民工群体开始,已经历了近27年的政策发展演变。然而目前农民工群体所面临的问题依然深刻而繁多。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工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和发展。东北财经大学徐祥运教授以大连市为例,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进行研究,既分析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的制度因素,也研究制度制约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行为选择。广州大学助理研究员吴俊英等认为,从目前的农民工政策困境来看,农民工政策的全面转型是适合城市与农民工和谐共赢发展,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实现农民工问题根本治理的必然政策路径。西部地区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制约以及自身的特点,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成为了更加困难的系统工程,面对这一基于乡城劳动力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现实课题。兰州大学人口与社会研究所陈斌研究生以社区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城市农民工专属社区在实现农民工城市融入方面的功能,提出了通过构建社区这一场域以改变农民工固有的惯习,并推动和实现其城市融入的路径模式。对于西部地区乃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周芳苓助理研究员等从“两欠”(欠发达、欠开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通过客观、真实的揭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职业人群的生存状况及特征、融入困境及表现,旨在科学解读当前该群体在“两欠”地区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从生存状况看,当前“两欠”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呈出就业形势不乐观、经济收入不理想、生活状况畸形化等特点;从融入困境看,则呈现出复杂而多元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现实困境、心理困惑、维权危机、社会失范等。长春工业大学曲海峰讲师认为只有生活方式城市化才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内在理路,并从概念辨析入手,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现状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为具体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提供一种参考。
厦门大学胡荣教授等运用定量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第一,社会资本中的普遍主义信任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普遍主义信任水平越高,则精神健康就越好。第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差异趋同因子对个体的精神健康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也就是农民工感觉到自己和城里人在文化价值观方面、经济社会地位方面越接近,则他们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好。其次,心理认同对个体的精神健康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农民工对城市、城里人的心理认同感越强,则他们的精神健康水平越好。也就是农民工对自己和城市关系的评价对他们的精神健康有着显著影响。最后,受歧视感对个体的精神健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第三,公平感受会对个体的精神健康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如果能促进公平感受,那么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就有可能得到较大的改善。在农民工的宗教信仰结构中,信仰佛教的人最多,其次是当地神灵、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没有任何人信仰道教。有调查显示,没有宗教信仰的农民工占3/5,有宗教信仰的农民工占2/5。有宗教信仰的男性农民工多于女性。信仰基督教的农民工多数是低收入阶层;信仰佛教的农民工中,人数最多的是中等收入层。信仰伊斯兰教的农民工中,高收入层的人数较多。信仰当地神灵的农民工中,中等收入层的人数最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卢国显副教授运用统计分析证实了宗教信仰与经济地位、社会距离与社会适应的相关性。交叉分析结果显示,宗教信仰与农民工的同乡会参与、社会冲突、安全感具有一定联系。宗教信仰促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缩小了他们与市民的社会距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小伟助理研究员则认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问题,必须建立起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农民工自我服务为一体的文化建设格局。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朱逸博士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风险形成的间接缔造者,同时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社会风险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涉及了生活、学习、教育、就业等诸多方面,对于处在“风险社会”中心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显得尤为重要。针对于这类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构建,所需要凸显的是主体现实需求的满足,诸如:福利服务制度、职业福利制度、“社区福利联合体”,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利于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最终实现市民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金小红副教授等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一组具有代表性的流动青少年的犯罪状况;并考察影响他们犯罪的社会成因,比较分析他们流动前后的几个因素的突出变化,从风险理论的视角,阐述社会环境风险给他们生存带来的损失性与破坏性,并据此提出了针对流动青少年的社会管理创新展望。因此,农民工能否实现农民工由农民群体角色向市民角色的整体转型,平等地融入城市社会,是关系到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有序推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
延安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所毛铖研究生等认为,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被称之为农民工的“附属品”,流动与留守儿童的受教育难问题与农民工问题一样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深层的体制原因,加上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阶段财政负担体制、现有教育有关政策法规的滞后,导致流动儿童上学难。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实行“居住地上学”替代“户籍地上学”;义务教育财政由地方缴纳,中央统一有差别拨付协调管理与义务教育“个人账户”相结合;将接受流动儿童入学纳入城市学校招生计划内和考核指标内;给予农民工子弟学校相关的政策扶持,成为解决流动儿童受教育难问题的政策出路。